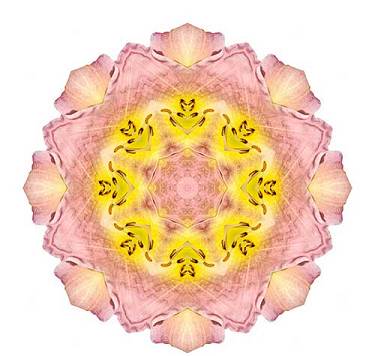图齐藏地摄影展:一个意大利人眼中的梵天佛地(2)-西藏频道-人民网
发布时间:2024-09-23 05:41:27作者:普门品全文网
图齐藏地摄影展:一个意大利人眼中的梵天佛地(2)-西藏频道-人民网
附:从故纸堆里走出来的生动图齐 对于图齐的藏地摄影展,本来只是想作为一个文化事件来报道。而在采访和查阅资料的过程中,一个立体丰满的图齐,从故纸堆里走出来。 黑白照片上的图齐,穿着厚厚外套、脸上带着浅浅笑意。 图齐是语言天才,除了母语意大利语,还通晓梵、英、汉、藏等多种语言。 1925至1930年,图齐以意大利驻印度外交使团成员的身份居留印度,在印度国际大学和加尔各答大学教授意大利文和中文。 中国国家图书馆可以公开查阅到的图齐著作有三本,分别是《喜马拉雅的人与神》、《西藏宗教之旅》、《西藏考古》,不过著者被翻译成为“杜齐”。 他给儿子起名为“阿难”,是一位佛陀的名字。 图齐本人的摄影技术很糟糕,他亲自掌镜的作品,被描述为“几乎所有的照片都显示出曝光和焦距失衡,画面抖动,还有无法合理解释的视图误差。” 图齐科研考察经费来源多样,他曾在文章中多次提到赞助商的品牌和产品,一张藏人手拿意大利面和可可粉的照片还被用做广告。